讲述/陈益源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俯拍视角下美丽的三平寺。图/陈曙光
何谓闽南?对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陈益源而言,这个词早就在他生长的地方扎下了根,而他则以日常之所见、历史之遗存以及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为之灌溉,并慎重地为其下定义。身为文化研究者,他带着文献,前往留下闽南族群生活印记的所在,从那些寺庙、楼宇、文书甚至一块残存的碑刻上,寻找两岸之间真切的渊源与共同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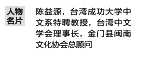
今年3月,陈益源(右)前往漳州平和进行田野调查,收获了珍贵的文书。
今年3月,我应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之邀,前往厦门参加“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学术活动,与全国台湾研究会汪毅夫会长对谈“闽台历史人群研究——罗汉脚、唐山妈、班兵及其他”的话题,之后我们俩又前往漳州,在闽南师范大学举行“闽南文化研究——田野、文献与田野里的文献”的对谈,第三天我来到泉州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主讲“金门田野报告:看得到却想不到的”课题。短短三天,来了一场短暂的闽南三地行,尽管第一次到闽南的记忆已远去,但于我而言,闽南早就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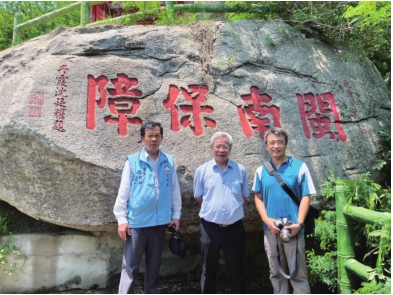 陈益源(中)到金门大担岛进行田野调查。
陈益源(中)到金门大担岛进行田野调查。
难忘的闽南印象
在无数次前往闽南的经历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10年9月因为承办“台湾—厦门文学之旅大学生夏令营”的缘故,让我有机会走遍闽南。这个夏令营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实地参访与两岸文学相关的现场,加深两岸学子对两岸文学的理解,进而培养互助关怀和彼此服务的品格,我接受了活动委托,带领台湾多所高校共四十位大学生到闽南,同时也邀请闽南地区的大学生到台湾参访,除了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泉州师范学院还有如今的闽南师范大学。
在厦门,我们参观了鼓浪屿上林语堂结婚的老宅,厦大校园里的鲁迅纪念馆以及南普陀寺;在漳州,我们走进位于平和县的林语堂文学馆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土楼群;在泉州,我们拜访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以及洛阳桥。其中林语堂算是体现两岸渊源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在漳州、厦门和台湾都留下了生活的痕迹,除了老家平和和厦门,台北阳明山上也保留了林语堂的故居。而我们安排的行程,正是希望两岸学子能够明白:想要对林语堂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就要走进他曾经生活的地方,无论是闽南还是台湾都缺一不可。而参加这次夏令营的两岸学子都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哪怕已经过了十几年,他们当中有些人依然还保持联系,这让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另一段在闽南的特别经历与我的外婆有关,外婆家就在鹿港镇东崎里的谢厝巷,小时候妈妈带我回娘家,眼盲的外婆都会用一口浓厚的泉州腔喊我的名字,我走到她跟前,她便摸着我的手,拿出卤好的鸡腿给我吃。2011年,我到泉州师范学院开了一场闽南文化的讲座,来到泉州,听着泉州腔调的闽南话,我自然想起了外婆,还有那难忘的鸡腿香,便在现场分享了那段童年经历;没想到两年后,我再一次来到泉州师范学院开讲,讲座结束后,突然有一位泉州师范学院的校友送上了两只大鸡腿,还贴心地附上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陈主任,不好意思,我手艺不好,鸡腿卤焦了,所以只能请师傅代为制作。也许没有您所期望品尝到的外婆家的味道,但却有泉州人满满的热情与祝福哦!”这张卡片我留下来,那两只鸡腿我便和黄科安教授一同分享了。
其实不止鹿港,台湾彰化、云林和金门以及泉州晋江这些地方同样有谢厝,我曾请教过舅舅,他告诉我,外公家很早以前就从晋江搬到了鹿港;而我父亲这边虽然没有留下族谱,但从祖先墓碑和神主牌位上可以确认,我们的祖籍乃是漳州漳浦。众所周知,历史上有许多漳泉移民前往台湾垦拓定居,他们与闽南故乡的联系,往往就体现在那些以姓氏命名的村落或地名,两岸恢复交流后,不少闽南籍移民的后代返回大陆祖地寻亲,他们想了解自己的家族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历经艰险抵达台湾,这样的追寻是很自然的,而且具有特别的意义。

陈益源(右一)到马来西亚彭亨州文冬县进行田野调查。
文献与田野调查
像我们这样从小在闽南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孩子,对闽南的一些民间信仰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当然,基于我个人学术研究领域的选择,我也在民俗学方面的研究倾注更多的时间,其中田野调查就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式,我时常往返台湾、金门、澎湖及闽南地区进行各种田野调查工作。
曾经我做过有关祖籍泉州南安的越南华侨黄仲训家族的研究课题,大家都知道黄仲训在鼓浪屿上兴建了不少别墅,其实他的父亲黄文华当年就是越南胡志明市数一数二的有钱人,为了了解更多黄氏家族的情况,2014年,我动身去泉州南安的黄氏墓园,据说黄文华的夫人就葬在这里。当我和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王连茂和王亦铮博士到了现场,却没有看到墓碑,正感到奇怪时,我看见一位老农正在墓园旁的田地劳作,便走上前问他,“请问这里是黄氏墓园吗?”他答“是啊。”我接着又问:“那怎么看不到任何一块墓碑呢?”没想到他指着我脚下的一块石板说:“你踏的就是。”在他的协助下,我们把那块石板挖了出来,恰恰就是黄仲训次子黄庆榕的墓碑,这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往往能发现不少体现两岸渊源的线索。我在金门做田野调查时,当地朋友给了我一份特别的文书,那是他在收集金门当地文书时,偶然得到的一份来自漳州的契书,上面写明:立契人陈八佾、王氏夫妇,将亲生二男陈武彬(1917年时16岁)同时皈依“广济祖师”“三山初夫子渧君”(文书中“三”“山”上下组合成一字)座下为义子,“伏祈佛光护照,神力加被,四时八节康宁,免诸灾劫,六时吉祥,多增福寿,富贵双全,长大成人,自当报答慈恩,永戴不忘”。这张契书展现了闽南一种特殊现象——“给神明当契子”,主要是在孩子体弱多病的幼童时期,不少父母会带着小孩到庙里祈求神明收作“契子”(闽南语中干儿子、干女儿之意),通常会立契一式二份为证,一份烧给神明存查,一份带回家保管。我好奇的是,为何这位立契人要让孩子同时皈依在二位神明座下,还有那位“三山初夫子渧君”究竟是哪位神明?
今年3月,借着到闽南参加活动的机会,我在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林晓峰会长、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院刘云院长等人的陪同下,特地走访著名的“广济祖师”祖庙——平和县三平寺,期待经由实地田野调查来解开谜团。此前通过调查,我推测“三山初夫子渧君”应是笔误,原来应是指“山西夫子”即关圣帝君,且极有可能立契人所在的庙宇同时供奉广济祖师和关圣帝君。当我来到三平寺时,发现寺庙内并无奉祀关圣帝君,不过我也有其他收获:通过翻阅三平风景区管委会编写的《三平寺志》《三平祖师分灵录》等在地文献,我了解到漳州确实有几座广济祖师庙内供奉着关圣帝君,算是给之后田野调查提供了新的方向。在我看来,田野调查与文献就是相互配合的关系,研究者应首先掌握若干文献,带着文献跑田野,到了现场既可以继续追踪,有时还可能在田野发现新的文献,这对于我们从事闽南文化研究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陈益源(右一)考察位于越南胡志明市的金门会馆。
陈益源(右一)考察位于越南胡志明市的金门会馆。
牵起两岸情缘
在我看来,研究闽南民间信仰的价值在于,了解闽南人信仰的动机,不仅是广济祖师,闽南地区还有给临水夫人、注生娘娘等神明做“契子”的风俗,老百姓对这种事抱着虔诚的态度,并慎重地采用立契约的方式。立下契约后,“契子”在神明诞辰日时要前往寺庙上香祈福,一般等“契子”满16岁后,父母会再带着契书回到庙中拜谢神明庇护,并与金纸一同焚烧,象征着解除契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举动,多是他们在孩子生病或难养的时候,所寻求的一种心灵慰藉,动机就是为了保护孩子。相较于其他社会变化幅度更大的地区,闽南有着丰富的民间信仰,闽南人更重视自己的文化与生活中的信仰体系,这些深深影响着闽南人的生活观念与处世习惯。
假如以方言区来区分,除了闽南三地,台湾、潮汕地区跟闽南同样是紧密相连的,许多文化也是共通的。我十几年来往来闽南和台湾,参加各类学术研讨、文化交流活动,与闽南地区一些研究专家、学者以及高校、文化机构始终都期望能借此强化闽台关系,同时也探讨双方未来在闽南文化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哪些合作探索。比如2019年,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与金门县文化局主办,台湾成功大学文学系、金门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台南府城观兴文化艺术基金会协办的“2019闽南文化暨闽台科举学术研讨会”在泉州召开,我们所关注的便是闽台两地的科举文化,因为研究金门和台湾的科举制度,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与闽南的联系,特别是台湾不少秀才、举人和进士都是来自漳泉一带的移民家族。研讨会以闽南文化与科举制度为题,不仅通过翔实的史料阐述科举制度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还深刻切入了两岸亲密无比的历史脉络。
两岸频繁开展闽南文化学术研讨,这些交流所带来的丰硕成果也在其他领域发挥着联结两岸的影响力。我在大学教授闽南文化,更多的是从学术研讨角度出发,不过如何将学术研讨的成果进行更多元的转化,例如资讯化、AI化,让更多社会层面的人共同参与,也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譬如两岸宫庙的交流同样非常频繁,除了日常拜访,像金门浯岛城隍文化观光季、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等民俗节庆活动也尝试着吸引年轻一代关注传统文化,包括设计开发相关的文创,用新媒体的方式介绍传统文化等。这些行为的背后,彰显的是对于闽南文化如何与当地社会契合的思考。在我看来,闽南文化是建立在闽南语系的基础上,同时又能够超越语言的限制。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当闽南人离开闽南地区,他在新的地方自然会产生新的关系,比如迁徙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地的闽南人,自然就会将在地文化与闽南文化融合,由此为闽南文化赋予新的特色,而迁徙到台湾地区的,在这方面就更明显了。因此无论是研究闽南文化也好,推广闽南文化也罢,应该将视野转向更广泛的“闽南”,进而发掘出更多元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