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黄克全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金门籍作家黄克全对闽南的“再发现”,如同在情感的驱动下,洋洋洒落写下的一首长诗。当中诸多现实的、想象的意象不断交织,多重时空下的闽南也在他的思绪中不断被重组、再结构,他从这种时间的跳跃中寻找闽南文化的内核,为金门家乡寻找文化的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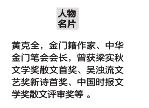
金门与厦门,仅隔着一道海峡而已。对于我父母那一辈人而言,厦金两地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一日共同生活圈”,他们通常早晨从金门官澳附近的港口搭乘小渡轮,到厦门采买完生活物资后再搭船返回。由于两地说的都是闽南语,交流起来并无隔阂,他们对厦门,或者说对闽南的印象往往更直接和更具现实生活。而我们这一辈,对闽南的了解更多是从情感延伸的想象为开端,继而再从想象碰触到现实。

泉州开元寺内“桑莲法界”匾额,暗喻了开元寺是由紫云黄氏始祖守恭公舍园建寺而来,桑树开白莲的传说。黄克全的家族出自紫云黄氏,他的开元寺之行正是为了寻访先祖的足迹。
两次闽南之行
我第一次到闽南是源于一场活动,2012年10月,福建举行了一场“自由行走 情感两岸”大型征文颁奖活动,来自海峡两岸各行各业的作者踊跃投稿,我太太王学敏的作品获得二等奖,我以家属的身份陪她前往平潭参加颁奖典礼。我们结识了当年荣获一等奖的作者潘春鸣,他是一位在大陆创业的台商,言谈间我们发现彼此都有相似的两岸渊源,潘春鸣突然问我,“黄老师,您老家应该是在泉州吧?我开车带你们去参观泉州的开元寺。”
众所周知,正是泉州郡儒黄守恭无偿捐献了一百多亩的桑宅用于建寺,才有了今天的开元寺,此后黄守恭的子孙都以开元寺中的檀越祠为祖庙,以“紫云”为堂号。黄守恭的五子后来分别迁徙至南安、惠安、安溪、同安和诏安等地,其中第四子黄纶先定居同安开基,后有一支黄氏宗亲移居金门繁衍。我们家也属于紫云黄氏的支脉,当我真的置身于这座千年古刹内,意识到这是先祖的产业,第一次因血缘、亲缘而备受感动。此外,我还注意到开元寺内的一副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这是南宋大儒朱熹所撰,他曾出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彼时金门正属于同安县治下,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曾经到金门视察和讲学,当时我就想起,金门浯江书院内的朱熹雕像及朱子祠,这也证明了闽南与金门之间的深厚渊源。
第二次闽南之行我来到了厦门。2017年7月,我受邀前往厦门担任第四届龙少年文学奖的评委,其间,主办单位特别安排评委们参观了鼓浪屿、曾厝垵和南普陀寺。当我登上鼓浪屿,想起了母亲曾经告诉我,在她还是小女孩时,因为日军攻占金门,他们一家先是逃到了厦门,后来因为厦门本岛也遭到轰炸,他们又涉水前往鼓浪屿避难的往事。那天,我在鼓浪屿的海边站了很久,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母亲就站在我身旁,和我一同看着当年那个趁着退潮,匆匆蹚水奔向鼓浪屿的幼小的身影,或许她头顶上方还传来飞机恐怖的轰鸣声、身后则是炸弹落下燃起的灼热之火。时过境迁,当年的战火早已消弭,而今我静静地看着面前激荡的海浪,一股激动的情绪却不断涌上心头,久久无法平复。
回到台湾后,我很快便写出了《鼓浪屿之行——80年后,重返母亲当年逃难之路》这首诗,其中“蝴蝶般的小女孩回眸一笑/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她知道我就是她的眼睛/她的火和冰的全身吗?”这几句,就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情写照。虽然我并非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但我觉得自己是通过创作在与母亲对话,这首诗歌中还有众多的意象,有些是借母亲之眼而“看见”的,有些是我自己所“看见”的,我和母亲的双重视角在不断切换,因此诗歌整体呈现出偏魔幻写实的味道。就我个人观点,写实主义并非客观的对现实的模拟,而应该是透过我们的想象实现对现实的模拟,这属于第二层模拟:即借助文字这一媒介,撕掉一些纯粹的现实。恰如我对闽南的初印象,也是透过第二层的想象,去打破现实的隔阂,从而塑造出我心中的闽南印象。

黄克全初次到访鼓浪屿时,曾站在岸边远眺母亲当年从轮渡涉水前往鼓浪屿的那片海域,图为人们在鼓浪屿的港仔后海滨浴场戏水。
破碎与整合
在担任第四届龙少年文学奖评委时,我和其他大陆评委看了很多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青少年的投稿。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感受就是两岸青少年之间基本没有什么隔阂,读他们的文章可以感受到,无论是文学程度还是思考方式,双方都不存在很大的差别,情感上是可以相互沟通的。
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应是两岸当下文学的走向基本趋同。如果说从前海峡两岸的文学创作更倾向一种“大叙事”风格,创作者有共同关注的创作主题,主要是凸显社会发展及时代的变迁。那么当下的文学创作则更突出个人主体性,也就是更关注偏个人内在意象的一些东西,这也是随社会的发展而自然发生的风格转向。关于这个问题,我太太也提到自己的看法:她觉得像朱天心、蒋勋这些作家擅长描写自己情感上的乡愁,以及为那些背井离乡的老兵发声,那些作品大多具有历史的重量且情感非常浓烈;反观现在中青代作家生活在资讯爆炸的时代,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更多更杂,反而他们的创作不太在意时代的氛围感,而是更关注个体,且受网络化的影响更明显。
在我看来,现在年轻一代创作者追求的是后现代主义,他们强调破碎和个人分化,我的观点还是比较偏向70年代,强调的是整合和形成体系,目前我正在着手策划《薪传:金门当代文学大历史》,当中不仅涉及金门文学,我还准备将大陆、台湾以及港澳地区,甚至包括南洋一带与金门相关的文学进行整合。因此在这本书里,我计划收录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地的华文作家,同时我也希望能结合两岸文学界的学者专家的力量,共同投入到这个计划中来,因此我也邀请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徐学教授、刘奎教授,还有闽南师范大学的陈庆元教授,请他们担任论述者,为书中的华文作家做更严谨的论述。
在统筹汇整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特别的收获,比如我接洽了台湾暨南大学的黄锦树教授,他出生在马来西亚,后来赴台读书并留在台湾工作。我看到他发来的简历上提到自己祖籍福建南安,就跟他说:“我们可能都是黄守恭的后代呢,你应该是长子那一支脉,我是第四子那一支脉的。”他同意我的想法,还提到南安有很多像他们家那样下南洋,迁徙到马来西亚定居。这个小插曲让我更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跟闽南文化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从金门可以清晰地看到厦门观音山一带。
“流离”的闽南
在撰写《薪传:金门当代文学大历史》计划案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金门文学的主体性究竟是什么?从历史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五胡乱华”大批汉人从中原地区迁徙至闽地,之后还有跟随王审知开闽、陈元光入闽而迁徙到闽南三地的众多宗族,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又陆续迁往金门、台湾开基。从这段迁徙历史来看,闽南文化是发源于中原,随着中原汉族迁入闽南,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而形成的,金门和台湾深受闽南文化影响,也是由于宗族的迁徙,具血浓于水的牵连。因此,思考金门文学的主体性,其实也是在思考闽南文化的主体性。
谈到闽南文化的主体性,我认为是一种“流离”意识,它应该是一体两面的:大陆性格和海洋性格。大陆性格是偏向安土重迁,相对比较封闭保守,因为大部分族裔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海洋性格是偏向积极进取,游离且带有一种不确定性,这是受海洋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两种性格听起来很矛盾且吊诡,在我看来,这两种性格辩证性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依靠我们的宗族观念维系住了闽南文化的发展。举个例子,譬如闽南人“下南洋”的历史,他们敢于前往未知的地方打拼,在南洋站稳脚跟后,他们选择借助宗族相互抱团,比如南洋、日本各国就有很多福建会馆、八闽会馆等,赚到钱后他们大多也是寄回家乡盖新楼、修祠堂,可见其心系故乡、光宗耀祖的思想。早期金门人要下南洋,都是先搭乘小渡轮到厦门,再从厦门港坐大轮船到东南亚,曾经在日本长崎还有金门人陈国樑父子创办的泰益行,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跨国独资企业,业务还拓展到中国、俄国及东南亚等各地,这个例子展现的便是闽南文化中积极进取的海洋性格。
对闽南文化的这些思考,也影响了我的创作。2017年的厦门之行,除了鼓浪屿,还有另一个地方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那就是曾厝垵。当时带我们参观的厦门友人告诉我,曾厝垵是厦门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之一,我在那里看到了停泊在海滩边的渔船,当地还保留着不少古朴的老房子,这些场景令我想起了小时候长辈口中的“下南洋”故事:我的一位叔叔就曾下南洋创业,但他最终并没有成功,也没有回到金门。我想,世上其实还有很多伟大的失败,《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出海捕鱼,最终并没有将鱼带回来,他失败了吗?然而他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却感染了很多人,所以他是伟大的失败者。
以结果论,我叔叔是失败者,可他最初却是充满了冒险进取的精神,也很努力工作,那么他的失败是不是应该打上引号?我又想起林尔嘉这位出身台湾板桥林家的商绅,他的家族早年从福建迁居台湾,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经营成为台湾首富,后来不满清政府“割台”而举家迁往鼓浪屿,为厦门市政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海峡两岸及南洋都颇具声望。我构思的小说,就是召唤这两位人生际遇截然不同的灵魂,在曾厝垵展开一场关于成功与失败的对话。这篇小说我已经陆陆续续写了五六年,一直在修改,他们之间也许还会发生更多的故事,最终我还是会完成这篇小说,也许是对我那趟闽南之行落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